<ul id="wcmie"></ul> <strike id="wcmie"></strike>
<ul id="wcmie"></ul> 

 聯系我們
聯系我們 地址:
地址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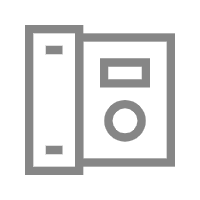 電話:
電話:
 手機:
手機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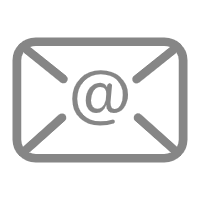 郵箱:
郵箱:
沖擊之七:依賴的問題
團體里有一種成員,永遠躲在后頭。他們不發表自己的觀點,不涉身諸事。但是卻對團體有著很強的歸屬感,很少遲到,非常不愿意團體里有人退出,仿佛每個人對他/她都很重要。
這種鮮明的反差也會令人困擾,究竟他/她是關心團體呢,還是對團體里的事漠不關心呢?這里面有一種非常的在意,但是同時有一種非常的害怕。讓自己不出來,這樣就不會犯錯誤,不會說錯話。讓自己顯出一副“事不關己”的樣子,其實是對自己的一種保護。
想象一下,一個小孩從小被各種標準環繞,在中國教育體系的模式下,他/她必須遵循大人給規定的一切。而他/她自身的感受、看法、意見從來不被過問,不被尊重,甚至被粗暴地壓制。為了生存,他/她必須討得大人的歡心,那么他/她學會的就是不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,隱藏自己的感受。久而久之,屬于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就消失了。換句話說,他/她自己就消失了。
人成為功能性的人,符合文化教育下所要求的標準,可以從事工作,賺取生存,卻由于自己的不存在而失去了生命與樂趣。在團體里,這樣的“消失”甚至是他/她自己的選擇。因為他/她對這個世界的體認就是,不被看見、不被聽見意味著安全,意味著可以存活下去。讓自己成為隱身人,如果在團體里是這樣,那么在現實中也會是這樣,隱身人的滋味想必是不那么好受的。那種自己不重要的感覺,是任何人都不真的愿意承受的。這種沒有自己,只聽他人的,是一種依賴,一種很極致的依賴。
團體里還有一種依賴,是依賴一個強有力的對象。很多時候是這個對象可能是治療師,或者一個重要的組員。這是一種對權威的依賴,因為權威那里有“標準答案”,可以從那里獲得自己是正確的這樣的確定感。這在中國文化教育背景下非常常見,要尋求外在的“標尺”。在團體里,這種依賴的體現是,說話時總是只對著那一個人說,仿佛只需要他/她的聽見,需要他/她的看見。即使是對其他組員說,目光也經常瞟向那個重要的人。仿佛得到他/她的認可是在團體里的最重要的事。
這樣的存在仿佛在說,只有那個強有力的人存在,自身才得以存在,如果那個強有力的人不在的話,他/她自己就陷入迷茫、失落、無所適從。
中國的文化教育需要特別對這種依賴人格的養成進行反思。如果孩子的成長不是依據自己內在的一種生命力,一種對自己誠實認真的體認,而是單向地遵循外在的指令、規范、標準。那么,內在自我的被扼殺將會付出的代價是創造力的喪失,生命喜悅的喪失,人可以被塑造成有用的機器,而失去了存在意義的空殼將會是種多大的悲哀。
沖擊之八:表達需要的困難
當一個孩子覺得自己的感覺不重要,自己的存在不重要。或者活著主要就是為了達成父母的標準、父母的需要時,他/她從小就覺得自己不具有表達自己需要的權力。他/她不配去擁有好的、有價值的東西,因為他/她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取悅其他的人。
所以,對于自己被愛、被關注、被聽到、被看到的需要在團體里往往會采取曲折、迂回的方式。也就是說通過先給予別人關注、先去傾聽別人、幫助別人。而把自己的需求壓下來,一直等一直等。有的時候這種退讓會持續好幾場,然后里面由于有一種不能滿足的饑渴和一味的退讓,升起一種憤怒。
這種憤怒仿佛是一種無名火,因為它很難找到發出的對象,于是往往就轉為對自我的攻擊,嫌惡自己、厭棄自己。或者這種憤怒向外發出,隱含的信息是,憑什么我給了你們那么多,你們卻不能給我?!
這里面仿佛有了一種“交換”,前面的付出好像是為了給自己“賺得”回報的資本。沒有前面的付出,自己就沒有資格要求回報。但是與此同時,這也使得自己前面的付出不再單純。
因為那沾染上了交易的滋味,讓自己付出的關愛不再是真正的關愛,而是交換的代價。這就使得關系的本身蒙上了一層陰云,并且也使得當事者的內心有一種讓自己感覺低下的陰影。仿佛自己是一個情感的乞丐,總是在等待著該輪到自己的時候。總是在等待著別人作為回報主動向自己付出,這種等待往往致令內心委屈又脆弱,但是為了掩蓋這種脆弱,當事者常常向外界發出的是指責“你應該……”,它隱含的意思是,我都為你做出了這些,你應該……
它所表達的委屈是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樣地給我一些關愛,但是這種內在的“交易”衡量往往不被對方甘心樂意地接受,于是帶著憤怒和委屈,人與人的關系便疏遠了。
沖擊之九:對錯的問題
在中國的文化教育下,孩子從小被教導的就是要做對,對錯成了衡量一切的核心。也就是說,關鍵的不是自己的切身真實感受,而是是非對錯。
因此在團體里,什么是對的,是大家最為關心的。早期團體里的不安,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說話,應該依據什么法則,應該往哪個方向去,誰規定你的對錯?
團體成員往往把目光投向治療師,團體的帶領者。當帶領者沒有給出任何規則、對錯的標準時,團體里會彌漫著焦慮。因為沒有標準,所以做事的依據是什么呢?所以害怕出錯使得許多成員采取觀望、隱藏自己,令自己在暗中摸索出規律,才能去行事。
而團體中所鼓勵的卻是感知與表達當下的感受,這與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截然不同。當下的感受是重要的,無論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,都鼓勵被表達。
你的感受是重要的,意味著你是重要的,并且感覺沒有對錯。對同一件事,團體成員可以有不同的感受,那是很正常的。沒有對與錯,只有不同,而不同被尊重,也就是你被尊重。
如果你不表達你的感受,那么團體就缺失了你獨特的那個部分,團體因此會損失了一角。這個理念讓個體的實存得到尊重。不再是一味以某個理想的目標、理想的自我為準則,而是讓每個個體的聲音被聽到,每個個體的存在被體察。團體因此而豐富,而立體、多元化,具有生機和創造力。
團體向組員傳達的信息是,重要的不是完美,而是完整。而這個完整是讓每一個部分的你,每一種感受的你都顯露出來。無論是陽光的,還是陰暗的,當你更完整地顯露出來,活出來的時候,團體的活力就增強,團體的完整性就增強了。
沖擊之十:誰來負責
在中國人組成的團體里,大家起初對表達負面的感受非常有顧忌。因為非常擔心告訴對方自己真實的負面感受,會傷害對方。所以在被鼓勵真實表達了以后,常會在自己內心產生內疚,覺得自己做了對不起對方的事。這里就涉及到了一個問題,就是如果由于我的表達致令對方產生了某種感受,那么是誰來對這個感受負責?
提起這個問題,又涉及到了依賴的問題。極度的依賴模式的成員會認為,你的這句話,你的這個眼神,讓我感到了受傷害,影響了我的工作,你們這樣對待我讓我的情況更糟糕了。這樣的指責,是為了激起對方的內疚感,希望對方為自己不好的情緒負責。
事實上,如果不是自己允許的話,沒有人能傷害到自己。換句話說,每個人的感受,只有自己能為之負責。假如他人的話激起了我的負面感受,比如我感到受辱,那么這種受辱的感受是從哪里來的,是什么使對方的話勾起了我的受辱感。
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對方的話,而是在于自己的內心。那是自己的哪一個兒時的經歷致令那個受辱的種子埋下了,而今那種負向的能量被激起來了。去探索那個受辱的感覺,需要從自己的內在入手。
一個坦誠的真實的回饋,可以打開一個重要的工作。所謂的讓對方受傷,其實是使得工作的機會升起。我們不為他人的感受負責,只為自己的感受負責。當自己有負面感受時,也從指責別人的位置上轉回看入自己,這是在團體里的重要工作,就是對自身負責任的方向性扭轉。
沖擊之十一:別人的東西
有一次團體里的成員在講早到的時候,想喝辦公室里的咖啡,但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。感覺上這是別人的東西,所以仿佛應該問一下,但是問了又有可能被拒絕。自己曾經就拿來喝了,但是心里不踏實,仿佛做了一件偷偷摸摸的事,于是就硬著頭皮問了工作人員,當得到認可的時候,內心里一下子放松了。
在那天的團體里,也恰好涉及到關于三角戀情的議題。別人的東西去拿的話,內心里會有所顧忌。別人的人去拿的話,會是怎樣的呢?那是一種痛苦的感受,雖然可以告訴自己不去顧忌自己的情敵受傷與否,但是莫名的,去拿別人的東西,心里的踏實感就是沒有,心里的痛苦感卻異常清晰。
前面提到邊界的議題,這里也再次涉及的是邊界的議題。關于我的,和他人的。邊界的清晰,使得國與國之間平安共處;邊界的混淆,使得戰爭頻發。個體角度講,爭奪所有權,關乎自身幸福問題。國家角度講,關乎領土主權與尊嚴,兩國勢必寸土必爭。
但是被侵犯的感受里包含著受屈辱,而這種屈辱的感覺,并不是只在被侵犯者那里產生。在侵犯者那里同樣會產生。一旦邊界變得模糊,爭端開啟。關系里勢必包含了不被尊重,不被尊重領土權、不被尊重所有權、不被尊重了一種秩序和一種人的尊嚴。
在團體的工作里,當團體去到越深的地方,團體成員在越深的地方相遇的時候,就越發現,人與人之間的感受是相通的,動力的流通是一而貫之的。所以,當所施者所發出的力作用在承受者那里,同樣的感受也必定返回到發出者,施者與受者是一體的兩面,是不可分割的。
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,而是一個幸福如何達成的問題。人永遠不能達成局部的幸福,除非他/她顧及的是整個體系、整個大局的幸福。在團體的工作里,這一點非常明顯,一個成員的勇氣和突破,帶給整個團體突破和勇氣。一個成員的獲益是整個團體的獲益。一個成員的受損,是整個團體的受損。
在西方的觀念里,注重表達個體的需要,鼓勵直接表達個體的需要,鼓勵個體去行動以達成需要的滿足。但與此同時,也強調邊界的議題,沒有經過許可動用了他人的東西,心里會不踏實。去尋求對方的許可,就有一種張力,因為可能被拒絕。但是出于尊重的考量還是去征求對方的意見。得到許可,心里頭就踏實地享用那杯咖啡。但冒的風險是,如果沒得到許可,同樣出于尊重,就愿意放棄享用那杯咖啡的機會。
這么做的益處是,由于尊重了他人,因而自己也得到了被尊重的感覺,這時內心的體驗是踏實,而這種踏實是冒著被拒絕的風險所達到的,但即使被拒絕,如果自己內心允許并接受這種被拒絕的可能性的話,那種踏實是依然存在的。
沖擊之十二:性的議題
在中國人的團體里會談及性的議題嗎?中國人一向對在公開場合談性比較保守,因此我一直把這個議題當成只有在西方團體里才能暢所欲言的領域。但是,在我們開放式團體(長程團體)里頭,雖然大家在非常長的時間里對性閉口不談,可突然有一天,大家就那么坦然地談了起來,并且相當敞開也相當深入。自此我才知道,中國人的團體里也談性,只是需要更長的一些時間,需要更多的一些安全感。
在團體里,任何的感受,任何的議題,是沒有禁忌地可以談論的。尤其鼓勵表達的是當下的感受,當聽到任何成員在說著什么的時候,自己內心里產生的真實感受是什么,自己對他人,對整個團體,對自己的感覺、想法是什么。團體越能聚焦在此時此地,就越有充足的能量在流淌,所有人所經驗到的自身活力的流淌就越多。
歐文亞隆人際互動的治療團體是一個多角度、多層次的此在、當下的呈現。在團體里中西文化相遇,西方心理學理念給了中國慣性思維模式許多撞擊,使我們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和看待問題,使我們質疑自身早前從沒有質疑過的定勢。在這種搖動中,有一些新的機會得以敞開,那是從碰撞的裂口中涌現的生機,使得個體有機會成長的生機。
版權所有 © 2025 廣州心燈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備案號:粵ICP備2020114672號-1